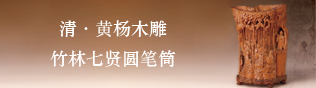《无题》
荷叶清风入佛堂,
闻茗禅坐飘檀香;
翻阅宋瓷赏幽雅,
穿越人文气宣扬。
翻阅定窑瓷器随笔。一个让人神往的时代,一个想穿越到哪儿去生活的朝代。书法上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绘画方面如徽宗赵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梁楷、牧溪、温日观等等院派和僧侣画家,瓷器也达到非凡的水平,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就诞生在宋代。 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定窑遗址,他是宋、金时期影响最广规模较大官民瓷窑场之一,自被发现以来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专著几部,涵盖了烧造历史、烧造品种、窑址情况已经器物上的铭文等等。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主烧白瓷的窑场。在宋代已经有文献资料有关定窑的记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苏轼《试院煎茶》诗词曰:“蟹眼已过鱼眼生……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倬红玉……”、叶子真《垣斋筆衡》曰:“陶器自舜时便有……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磁,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自元代晚期定窑逐渐衰落至停烧以后,也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没有看到文献资料记录,被遗忘。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叶麟趾教授在河北省曲阳县调查时,发现了定窑遗址,并在1934年所撰《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谈到:“定州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
二、定窑瓷器工艺和艺术特点
唐代白瓷水平最高当属河北省内丘县邢窑白瓷。除了邢窑之外,在唐代定窑、巩县窑、密县窑、耀州窑等均有白瓷烧造,但是总体质量水平都逊于邢窑;唯有定窑白瓷中质量精美者不逊色邢窑白瓷。到五代时期,定窑瓷器胎体变薄,形制仿金银器,颇有质感。立于大周显德四年二月《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石碑内容:“……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使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说明五代时期瓷器产量很大,以致朝廷派人收取瓷器税。到了宋代,定窑白瓷无论产量和质量均比唐代提高很多,产品也远销海内外。
定窑除了烧造白瓷之外,还兼烧黑釉、酱釉、白釉黑彩、铅绿釉(低温)、铅黄釉(低温)、铅黄/绿两色釉(低温)器物。黑釉、酱釉器物即“黑定”和“紫定”。明代人曹昭《格古要论》中曰:“……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俱出定州。”定窑里的低温釉瓷没有文献资料,也没有传世器物,于1969年河北省定县北宋静志寺塔基出土了绿釉净瓶、绿釉弦纹瓶、黄釉鹦鹉执壶和盖罐,则说明北宋定窑曾经以氧化铅作为熔剂烧造过绿釉和黄釉器物。北宋至金代,定窑瓷器以民用为主,但是由于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都很高,一度选为宫廷用瓷。
定窑白瓷工艺水平非常高,由于当地釉料中氧化钛含量高,用氧化焰烧成,因而釉色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感觉,给人视觉温润、柔和感强。在制胎选料上精心加工,使烧成后器物胎质洁白细腻。
定窑器物非常丰富,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具,如碗、盘、杯、碟、盏、盏托、渣斗、净瓶、壶、罐、枕、炉、盒、俑、动物、玩具等等。为了适应生产需要,降低成本,北宋定窑的匠人发明了先进的支圈“覆烧”工艺,把碗、盘之类器皿倒扣,放在内壁呈锯齿状的匣钵内,层层叠加。支圈覆烧工艺的优点有:1、这中工艺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可以大量节省空间,降低成本,使产量倍增;2、由于覆烧时器物口部紧贴垫圈,支撑范围大、重心稳、收缩均匀,能保持产品不变形;3、覆烧器物外底满釉而润泽柔美。但同时,缺点也明显,为防止器物口部与垫圈粘连,口部不能有釉,必须挂掉一圈釉,露出胎骨,这种毛口俗称“芒口”。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们常用金、银、铜等金属鑲在口沿,形成金釦、银釦、铜釦,不但掩盖了毛口之弊病,又让金属和洁白瓷釉形成鲜明对比,更显优雅尊贵。
定窑瓷器覆烧工艺产生时间众说纷纭,主要是三种观点:1、多数人认为定窑用覆烧时间在北宋中期;2、有认为是北宋早期;3、也有认为是北宋晚期。主张早期的观点,其依据是文献《吴越备史》记载:“太平兴国五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株。”这里所说的“金装定器”是否与芒口或是因覆烧需要慎重考虑。晚唐五代器物中有不是“毛口”、“芒口”也鑲金属釦;即使是芒口也未必与覆烧有联系,1969年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和净众院两座宋代塔基地宫共出土了一百五十多件定窑瓷器,有近十件有芒口但没有鑲金属釦。从《重建静志寺真身舍利塔铭》记载内容看,都是达官显贵、僧侣、信徒施舍供于地宫内。上述时间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属于北宋早期,故有观点认为覆烧工艺始于北宋早期。覆烧出现在北宋早期没有问题,但未必使用支圈窑具覆烧。静志寺塔基出土一件定窑白釉洗不是芒口也鑲金釦。说明鑲金属釦与芒口没有必然关系,也说明鑲金属釦器物不一定是芒口。鑲金属釦主要目的是用来装饰、提高器物本身价值。
定窑瓷器装饰方式主要有:帖塑、刻花、划花、印花、剔花、描金等等。从出土文物分析,早期多采用刻花和划花装饰,印花出现在北宋中期、成熟于晚期,流行于金代。早期定窑器物刻花、划花构图简练,莲瓣纹居多,莲瓣从一层、两层、三层至四层不等,纹线饱满、有浅浮雕感。也有其他纹饰,如蝴蝶、缠枝菊、海水纹等等。北宋中晚期定窑刻花纹饰精美,图案丰富而有变化、独树一帜。采用刻花与划花相结合方法,在器物里面或外部等刻出缠枝或折枝花卉轮廓,再用篦梳状工具在轮廓线里面划出筋脉。由于定窑瓷器胎体薄,不易深刻纹饰,但是通体施釉在刻刀深浅处留下釉色的浓淡厚薄变化,充满想象空间。
定窑瓷器所有装饰手法中,以印花最受人称赞,在宋、金时期所有瓷器使用印花工艺的,唯有定窑印花技艺独占鳌头,可谓印花之冠。
印花题材中,牡丹、莲花、萱草最多见,菊花次之。表现手法写实,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布局讲究匀称。云龙、蟠螭、走兽、禽鸟、水波、游鱼、婴戏纹等,这类纹饰经常与花卉组合在一起。如:孔雀多与牡丹相配,鹭鸶、鸳鸯多与莲花组合在一起。龙纹基本是三爪蟠龙,龙身弯曲,首尾相连。印花婴戏纹有婴戏莲花、婴戏牡丹、婴戏三果、童子赶鸭等等。其中婴戏三果纹较稀少,三婴、三果间隔排列,三果即寿桃、石榴、枇杷,三婴姿态各异,有双手拽树枝的,还有有骑树枝、立于树枝、坐于树枝的,体态可爱丰腴。总之定窑印花工艺具有图案繁琐、构图严谨、层次分明、图案清晰等特点。
定窑器物描金是指在白釉、黑釉、酱釉器物上描绘金彩花纹。南宋人周密撰《癸辛杂识-续集》中曰:“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绘,然后再入窑烧之,永不复脱。”这类描金定器传世极少。统计资料看,日本三件(白釉、黑釉、酱釉描金碗),故宫博物院三件都是金彩云龙纹白瓷盘,安徽省博物馆有一件酱釉金彩荷莲纹瓶。这些器物上的金彩都有不同程度脱落,足见周密所说永不复脱不可信。定窑匠人用大蒜汁调和金粉描绘器物,金粉本身就是需要粘性液体调和,之后才能绘制在器物上。定窑所在地区属于中国北方,盛产大蒜,同时气温较低,而黏性物质要求气温不能太低而冻结,刚好大蒜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至今,景德镇瓷绘艺人到冬天依然用大蒜汁调金描绘瓷器。
三、定窑器物铭文
从考古目前为止所见晚唐、五代、北宋、金代时期器物上题刻铭文几十种,内容涉及宫廷、官府、上流名士等有关。内容包括:“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东宫”、“徐六师记”、“易定”等题铭都是烧造之前刻划于器物之上。也有款铭是烧造成品后,被人刻划于器物底部的,比如有:“奉化”、“德寿”、“凤华”、“内司”、“寿成殿”、“寿慈殿”、“德寿苑”、“黄太后殿”、“供大官食合用”等等。上述铭文中,以“官”字款最多。
“官”、“新官”两种铭文所产生的时间顺序说法不一。一般人字面相对理解为“官”在前,“新官”在后;有人指出“官”字款是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简称;也有指出“官”、“新官”是“官样”和“新官样”的省写,是收取实物税的标准物样,“官”字铭文在北宋早期就消亡不见。由于定窑官民共用,落款铭文是否一定是供宫廷官用,需要结合金属器、漆器等其他宫廷门类署同类铭文作比对,可以肯定署这类铭文款器物,应该是官方认可,也以达到官方征用瓷器最低标准和质量要求。
在北宋、金代时期由于定窑烧造工艺水平独树一帜,刻花、印花白瓷名扬四海,在其影响下,许多其他瓷窑竞相模仿,形成产品类似器物体系。除了山西的平定、介休、盂县、阳城,四川彭县窑、江西吉州窑等等外,甚至影响到高丽瓷。这些瓷窑所具有的白釉刻花和印花装饰都与定窑白釉工艺、题材风格相似,这就形成了庞大定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