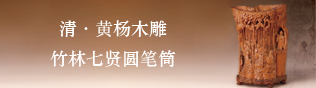在历经几千年的玉雕工艺演变历程中,所有的创新与变革都是源自于人类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所谓的传统都是相对的,时下较为流行的写意、简约的艺术风格相对于未来又何尝不是一种传统。说到简约、写意的本质大多是为了表达意象的目的,即以刻画局部或者简约的造像而言象外之意。然很多时候多数创作者都是单纯的为了简约而简约,因为省时又省工,却没有真正的象外之意,作品也就没有了灵魂。在此我借前人之谈以及我个人的浅薄观点谈谈玉雕的造化、心源和意象之间的关系。
唐代张璪有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乃是生活中的形象,可视为玉雕创作的原型,它包括了大千世界的天地万物。心源指的是以心为源,是创作者作为创作主体的思想、意念、情感与修为。造化与心源的关系是以借自然形象表现人的主体创作精神为主导,以造化为源,以心为本,合二为一而成意象。将心中的意象落实到玉雕作品上即为创作。同时也是有灵魂的创作。
外师造化——即以客观自然物像为师,大自然与人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这是经过艺术实践检验的真理,但师造化并不仅仅是指对景物的写生,还包括艺术家对生活、自然的深刻观察、研究与体悟等独特的心灵感受。
中得心源是外师造化的升华,是雕刻师将“外师造化”,所得的素材通过集中、概括、提炼、构思后在心中所形成的意象。心源是师造化的基础,造化是艺术家之心所师法的对象,二者相辅相成,相依相存。造化于外心源于内,内外的融汇于结合,即庄子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者。物即造化,身即心源,物、身融合而为象。故而造化与心源的融会贯通能使雕刻艺术家的创作外观于物,内发于心,立之与象,行之与刀笔,现之于器。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师字,确是运用得恰到好处。“外师造化”不仅仅是重视自然,而是要以师事之,以自然生活为基础,为源泉,为师承,通过“中得心源”的艺术加工与提炼,使客观的自然与生活达到具有艺术性的、理想化的境界。
因此玉雕创作的表现物像,不是单纯的刻画客观事物的外在表象,而是融合了艺术家主体思想意识与情感的意象形态,这种意象形态的形成与作为创作主体的雕刻艺术家本人的学识修养、人品素质、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技巧都有着有机的联系。“中得心源”的过程,实际上是把客观世界中的“物”,与主观世界中的“我”给予统一,交融的过程,而由此所产生的玉雕创作,即反映了客观生活物像的特征,又表现了创作者的情感因素,从而有了灵魂和鲜明的个性化色彩。
再谈到时下的简约写意的艺术创作,其实就是一种意象的表现手法。所谓意象也可以理解为人的主观意识作用下自然的人化。它并不特别看重自然形象的视觉真实,也不执着于物像的自然属性,只是把自然物像作为艺术创作中的“以物寄情”来表达作者意念的载体,从而使创作摆脱了时空的限制和自然属性的约束,从而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自由。清代戴熙有云“吾心自有造化,静而求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也”。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天地造物,随其剪裁,阴阳变化,任其分合;春夏秋冬可绘于一卷,南北景物,可现于一纸;四季花卉,可自由组合,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即超越自然表象,又默契着客观自然法则的幻化境界,为中国艺术风格所独有。在玉雕的创作中大多数人理解的简约写意就是做工简单或者局部刻画,其实不然真正的写意简约作品还是很讲究意的表达的或者理解的 ,当然市面上为了简约而简约的另当别论。时下很多艺人做简约多数都是以省工时和成本为目的,真正作品的表达也就无稽之谈了。当代的玉石雕刻艺术家创作都是相对传统的,对于突破自然和时空的限制束缚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当下的艺人们胆子大一点我们也未尝不可:“天地造物,随其剪裁,阴阳变化任其分合;春夏秋冬可绘于一石,南北景物可现于一玉”。很多人当看到一件作品有违背自然现象和事物规律时总会嗤之以鼻,认为创作人犯了很低级的错误,更谈不上艺术,在此我也想起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趣事,也算在此作为例证吧。
其一:苏东坡兴之所至,以朱砂色画红竹子。“或谓竹色非朱。”“则竹色亦非墨色可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苏东坡某日一高兴,用朱砂色画红色的竹子,旁边有人说,“竹子怎么会是红色的呢?”苏东坡看了此人一眼,说了一句:竹子也没有黑色的。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言:画事原在神完意足为极致,岂在彩色之墨与朱乎?
其二再如:“有客问,梅开之时有蝶乎?罗浮山见之。”这是齐白石题在画上的款书。据李苦禅回忆,有人问齐先生买画,指明要梅花,白石先生画完梅花后,觉得章法上不完善,随手在空出画了一只蝴蝶。买画人好奇问道:梅花开时怎么会有蝴蝶呢?白石先生题上句以作答——原来先生见过。买画者释然。时有二弟子在侧,买画者走后二人问老师,罗浮山冬天真有蝴蝶吗、白石先生答曰:“没有。”意思不言自明,此人不懂画,何必多言。此例只是意象的创作的一个缩影,它能使创作者天马星空,脱离自然属性所附,以此表达创作者的个人情感。当然这种意象的表达是有前提的,创作者要有丰富的学识、修养、扎实的技艺、甚至包括创作者的经历阅历,以这些为基础前提,在融合、提炼、聚与心源而发之。否则只是单纯滥情,作品本身徒有其形而无灵魂。
关于象和意的关系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创作的主体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象”,是艺术作品中的客观形象。“意”是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与思想情感。象与意是一种对偶的关系。《易经》中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观点,当语言无法把所以得心意全部表达出来的时候,以立象——即借用客观物像的具体化来尽意。象与意在中国的艺术创作中是充分体现主体思想情感的两个方面,象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借其表达意,象有着自身的形式规律与具体要求。
象又与物是相对应的。物是指具体的客观事物,即事物的内容,象是指事物外在的表现形式。当意运用语言的表达有局限性时,而运用象予以表现,却可以达到不用语言表达而尽意的效果,尽意是目的,立象是手段,立象是为了更深刻的尽意,这与玉雕主体精神的意境创作,最终要落实到造型与构成形式的表现上,并通过具体的立象达到意境创作的目的——尽意,在规律上是一致的。
象与物都体现了道,但因为道的精神是体现在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中的,这道因为受到诸多物象的干扰,便呈现出恍惚朦胧之态,我们要从某些象中去发现道,即从具体的形式表达中去窥见规律性的真理,则必须去除心中的杂念,细细地对其体味,揣摩并透过因有干扰而朦胧之态中体悟到主体精神,并能透过表象外在形式去发现本质,这也是南朝画家宗炳所说的“澄怀味象”与“澄怀观道”。
庄子则发展了老子的观点,《庄子外物篇》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是有限的,而意是无限的,只有真正的理解了意的无限,才能超越言的有限,也只有超越了言的局限,才能真正体验与把握无限而“得意”,而言的局限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才“得意而忘言”。在“得意”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象的形式就成为了一种附庸,象也就无关紧要了,故而得意忘象,这与得意忘言的道理是一致的,而且像越具体,局限性也就越大,为象而象是难以达到表现内涵丰厚,意义深远的“意”这一目的的。因此,艺术创作不能满足于有形有限的象,而应去追求表现无穷无尽之意的象,这就是象外之象。只有超乎了象外,超越了象的局限,达到大象无形的境界,才能真正:“得意”而“忘象”。
因此中国艺术家很早就认识到创作如果要表现宇宙生机与人生真谛,利用虚实结合,象与象外统一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主体思想的意的重要意义。远在隋唐以前,谢赫的《古画品录》即提出“若拘于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外象,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南朝宗炳也认为: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只有超乎象外才能得其环中。艺术创作要超越自然,必先超越感性认识,即超越有限,才能去把握无限。从而深刻的表现出作者的主体思想情感,表现真正的人生真谛之所在,艺术创作才能进入一个高超的全新的广阔空间。玉雕创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创作也应该有他的基本的内在原理。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造化为源,以心源为本,合二为一而形成意象。以循此理不说作品有多高雅,至少不会显得单薄,没有主体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