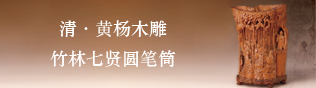和田玉先天有之,熔积、崩落、冲涮、形成、采捞下的籽玉,集宇宙日月光华之璀璨,神工鬼力,玄妙无穷; 任何一块和田玉,成之河清海竭,贵之麟角凤毛,在每个中国人的认知中,充满着无穷的神奇、尊贵和灵慧,而无限向往。和田玉玉雕古已有之,夏商周的琮壁玉圭,秦汉的玉衣玉章,唐宋的玉佩玉饰,明清的玉牌玩件……祭天佑地、神圣权威、儒心禅道和祥瑞避护的土地情怀,8000多年来都琢刻在器皿、牌子、玩件和首饰的条条痕迹块块之间;无论从形制、题材和工艺上,还是背后的用料、图形和文字中,深深的记录着每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商业、文化和生活的价值观。
可喜的是,当今的玉雕依然延续着平安、纳福和避邪的祥瑞基因,满足着不同人们的喜怒哀乐;依然继承着厚朴、圆润和精致的工艺巧设,体现着玉雕玉器的赏玩悟道;赋予了艺术和审美的独特价值,在传统样式上注入了国学文化元素,探索着当代玉雕在继承和发展上的时代语言。
传承,“乾隆工”的形神兼备
众所周知,“乾隆工”创造了中国玉雕的第三次辉煌,得益于乾隆帝的嗜玉成癖、爱玉如命,他把当时江南制玉好手调往宫中并设立如意馆,要求宫廷画家绘制图样,不遗余力的提倡和发展玉器制作的题材内涵、雕琢技法和艺术水准;又千方百计收集旧藏,创新品种,使得清代玉器制造达到了中国玉雕史上的又一次顶峰,也使得“乾隆工”成了玉器辉煌工艺和天工精品的代名词。
从目前故宫留承的《和田青玉蟠一心纹盒》、《和田黄玉兽耳方壶》、《和田碧玉果盘》、《和田青玉镂雕灵芝如意》和《和田碧玉山水人物方笔筒》等惊世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欣赏到“乾隆工”的玉料好、工艺精和抛光好三大特色。那种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工艺及历代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融会贯通的玉雕美感,让人赞叹。就如这件厦门市博物馆收藏的清乾隆《御制青白玉粉盒》,呈圆饼状造型的玉盒,不大却形制正气规准、简素雅致,柔小却质地细腻,玉色温润;玉盒带盖呈子母口,上下盖合紧密,开启自如;盒身通体素面无纹,琢磨晶莹朴厚;盒底微内凹成圈足状,十分惹人喜爱。其实,盒子是盛器,能容物,形式多样,用途广泛,女性可做粉盒、脂盒和饰品盒,男子可做章盒、玩物盒和饰品盒,可正可异,形制繁多;盒子可饰予各类象物,丰富中蕴含各种寄托,形成了功用私密、形制乖巧、雅致精美的逸感,广受历代文人的青睐,其中尤以玉制盒子为雅为贵、居高居尚。同样,我创作的和田玉子料作品《和田玉九龙宝盒》,也力求精琢出和田玉器物的大气和“乾隆工”的精致神韵,设想在当代玉雕创作中,探索着传统经典美与现代简约美的融合之道。
《和田玉九龙宝盒》取材于一块完整的和田玉子料,件大形正,玉韧质润,色白细腻,经整形后显示出正正方方的“仁义”之玉语、“君子”之玉德,方中隐正,正中寓润。设想中,首选器血,细选玉盒,一是为了用料考虑:玉型规矩,盒具中空,掏膛后余料可为它用,一料多用为省料惜料;二是为了价值考虑:玉雕求整,器皿为大,题材、工艺和艺术都为高,制作重器为显精工巧艺。设计时,作品为方盒状,有盖有身,膛余玉料琢刻为一镯一戒一章,一料多用,一料多器,实为敬玉尊玉;主题选择以龙为主的表现对象,拟附合与和田玉的秉性尊贵相适,精细以九龙为数的琢刻形象,拟以九字极数寓意着祥瑞的无边无限。完成后的《和田玉九龙宝盒》,形制四周方正规整,大面素清,方形敛口,内掏空的工艺精细、精致、精准,盖身指口运力合缝严密,稳适服贴;玉盒上下内外圆雕琢刻有云龙、香草龙、蟠龙和游龙等九条真龙,琢刻下龙的神灵、威严和智慧;只见盒身外壁腾跃的立体云龙,显龙在灵芝云海中翻云覆雨,龙眼炯炯有神似乎凝视、龙角张力四射似乎聚神、龙鼻呼之欲出似乎起跃,呈现出一幅生龙活虎的龙姿龙影……又见盒盖内壁隐藏的蟠龙,隐龙委藏于层层迭迭的玉润玉韧中,起伏、观望、上升,似乎是审时度世,似乎是察颜观色,感受到一种顺势而为的龙智龙慧……显隐间,刀到美就的磨就了生龙活虎、润泽流动的“玉龙”美感、刀到意成的记录下玉龙的飞龙在天、蛟龙在水的“神龙”寓意。
同样,“如意”也是“乾隆工”的常用题材,灵芝的聪秉、造型的演变、如意的寓赋,演义着只有中国创造的同音双关、谐音寓瑞的文化现象。我创作《和田玉如意摆件》作品时,在延续经典题材的造型、工艺和寓意的同时,根据和田玉材料的不同特性而设计制作,突出的是形象更真实生动、主次更分明变化、工艺更精致玲珑的诉求;用料上依形设计,依色俏雕,使得造型上的“灵芝”鲜活、厚实,在“灵芝”面上“点”的刻划,大小、上下和厚薄之间,显示出它的厚润度手感;在“灵芝”杆上“线”的营造,粗细、前后和交叉之间,隐藏着它的生命力量;用意上追求朴实、厚重和温暖的“如意”感,“点”与“线”形成的移动光点、流动柔线,无不折射出属于和田玉的温润温柔温暖的吉祥感受。
玉雕“乾隆工”的当代表现,在形的精确精准,《和田玉九龙宝盒》形制的静、九龙的动的琢刻,就在于当代琢玉人在传统继承中有了理性,有了设计;同样,玉雕“乾隆工”的当代表现,在神的生动灵动,《和田玉如意摆件》灵制的物象、如意的想象的记录,也在于当代琢人在经典传续中有了艺术,有了文化。而“乾隆工”的形神兼备,有了时代,有了鲜活。
探索,“海派工”的意象更新
当代中国玉雕的兴起、发展和变化,离不开海派玉雕的努力、探索和贡献,这种以城市意识、学院基础、精致工艺和现代审美为内核的“海派工”,奠定了当代玉雕所具有传承性的时代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以上海玉石雕刻厂工业中学为代表的工艺美术中学机制,决定了当代玉雕高峰的高度、长度和深度。我有幸成为近千名学生中的一员,既受过四年正规、系统的美术、设计教育的人,接受着素描、线描、雕塑、图案和玉雕等专业教育的学习;又经过三年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一对一传教,学习到了丰富、复杂和独特的”海派工”中“自然瓶”制作工艺。
“自然瓶”是器皿与人物、花鸟、走兽等自然物质结合的品种,以规准严谨的炉瓶为骨,琢以生动鲜活的自然物质为身,有盖,有膛,正面和两个侧面雕刻着仕女,可称为“仕女瓶”;如果设计上蟠龙,应该称为“蟠龙瓶”;假设是葫芦瓶加上梅花喜鹊的,毫无疑问就是“梅花如意瓶”……自然瓶应是不同品种、题材、工艺相融合的特殊品种,而“海派工”追求玉料上的完美无暇、造型上的丰富层次、对象上的精确造型、形态上的生动变化、工艺上玲珑剔透和作品上的极至满工在“自然瓶”上的运用,显示出了玉雕工艺的极致性、灵活性和独特性,我创作的《和田玉梅兰竹菊摆件》,就呈现出这种特质。
梅兰竹菊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存在于古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自然属性、功能属性、审美属性和精神属性,时时刻刻与人发生关系,让人喜悦、启发、明理,乃至悟道。“喜上梅梢”的好事降临、“桂子兰孙”的子孙满堂、“竹报平安”家庭如意和“松菊永存”的长寿平安等等,诉求的是梅兰竹菊的祥瑞符号,给人以纳福,以护佑;而人文情怀的梅兰竹菊“四君子”精神,梅的独立、兰的秀藏、竹的虚清和菊的傲放,成为了中国文人尊崇的高尚品德。而《和田玉梅兰竹菊摆件》,在尊崇和田玉子料厚实朴韧天然美的前提下,随形而作,从左到右设计着菊花、兰花、梅花和竹子,应用深浮雕结合立体雕工艺,为的是突出梅傲、兰幽、竹澹和菊逸的精神;左上角的数枝菊花似乎隐逸在峭壁凹崖中,屹立独放,在细透精雕中,展现出花瓣卷曲而富弹性、花蕊饱满而寓孕化的玲珑感,虬劲的枝干和四放的散叶,更显示出孤傲的风骨;右下方同样绽放的兰花,背阳处似隐似现,山阴下半遮半掩,却展露出不同的格调,兰叶逶迤的形态、曲折的生长和兰花花瓣的柔小、暗放的曲线,在软口工具的细磨精琢下,细巧中透出生命的韧性;而梅花的刻琢,恰恰磨就了一幅有故事的场景,在变化的应用深浮雕工艺下,密枝穿插、繁花怒放和喜鹊双飞,交叉重叠的层次中传达了“喜上眉梢”的祥瑞寓意,玩玉藏玉的人们从中可感受“功成名就”或“苦尽甘来”的望春情怀;背后个字叶叠加的竹叶和怀虚清直的竹杆处理,使得赏者观者有了中国书画中长卷般的连续阅读感,慢慢领会着和田玉与玉雕带来的自然美感和人生感悟。和田玉《梅兰竹菊》摆件创作中,我尤其注重作品底面的处理,在立体雕表现梅兰竹菊主体的形象生动下,弱化背后的玉面的处理,写意以表现出和田玉自然润泽的弧度美,点与线、线与面、复杂与简洁、玉质和雕工等的对比,似乎散发出深山幽谷中梅的独香、兰的幽香、竹的清香和菊的氤香,呈显出“四君子”正直,无畏,谦逊和文雅的诉求和审美。同样,和田玉《梅兰竹菊》插牌的创作,异曲同工中表现出玉牌的特点和美感,聚中的画面、层次的表现和深浮雕的工艺,更多的凸现文人画的画面感,使得平面雕刻下的梅兰竹菊,更富立体感、新鲜感和生动感。
其实,“海派工”既有着传统玉雕的滋润,又有着当代玉雕的精巧,创作出的作品都会蕴含着“乾隆工"的基因。故宫藏品《和田青玉船》,厚朴内敛,稳重致中;同样船板船舱,平平实实,同样的船竿船窗,粗粗厚厚,这是"乾隆工”的意识、工具和工艺的时代性所决定的;我的《和田玉子料船》,细致、精巧和丰富是“海派工”玲珑剔透所至。看看,一样的大小前后二艘木船,我追求的精致,精致了船沿的弧线角度、船橹的曲线粗细,尤其用极细工具挑出的直线曲线、圆角方角,呈现出变化而有统一的美感;再看,一样的前二后一的三个人物,我则不过把后边人物挪到了小船上,虽然丰富了层次感和可看性,也增加了雕刻难度,尤其是人物动态的前仰后俯、衣纹的流畅转折和关系的亲疏交流,更是在当代教育中写生速写所掌握的结构所能够表达的。从时代上来看,“海派工”相比“乾隆工”,肯定是工具更细更多、机器更快更好、工艺更丰富更多样、思维更理性更宽广,当代琢玉人没有理由在用料、内容、工艺和文化上,不超过古人、不超越过去;“海派工”相比“乾隆工”,追求更多的是意象、意境和意趣,那种个性化的表达应是当代玉雕的价值,也是自己的追求。
和田玉与和田玉玉雕走到了今天,已是中国历史上好料好工相聚的最好年代,如此质细润韧、皮油色红和玉脂白细的籽料,连康熙乾隆都不曾见过想见,皇帝只能感叹生不逢时;如此形制丰富、圆润精致和俏色巧雕的作品,艺术性、文化性和人文性已攀上了有玉雕历史以来的新高度,而成为最具现代文明基因的中国语言。如此,作为和田玉与和田玉玉雕从业者的自己,在玉料日渐稀少、玉雕日渐商业和玉意日渐浅人性化的今天,更应身体力行的珍惜它、善待它,并雕琢好每一件作品。